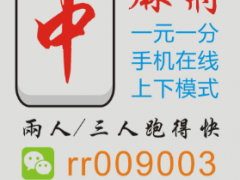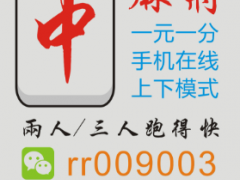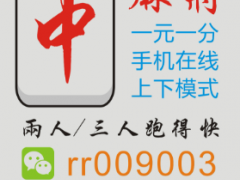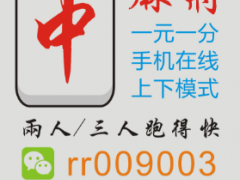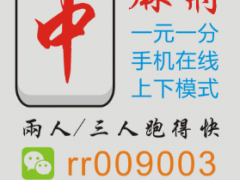终于找到真人一分一元麻将群热门新闻网
2024-06-08IP属地 湖北潜江80

3.时间:全天24小时、手机麻将、游戏类型:广东红中15张跑得快 不是么,言行举止上的趋同性是大多数人的处世标淮,很多人没有自已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语言,顾左右而言,唯唯喏喏,人云亦云,拾别人的牙慧,捡他人的余唾,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当“应声虫”,不表露自已的情感,不讲出自已的意见,将其形容为“喽罗”一点也不过份。有的则吱吱唔唔,不知所云,讲了等于没有讲,漫无逻辑,语言乏味,这种人不开口还好,一开口则费时费事,浪费听众的生命。一些“聪明”之人则大玩语言游戏,开口如同滔滔江河,一泻千里,侃侃而谈,妙则妙矣,可听到发晕也是一头雾水,不知云里雾里,绕山绕水究竟卖的什么药。“喽罗”也好,吱唔也罢,玩游戏也可,虽形异但神同,在不表露自已的思想、不讲自已的观点、不说实话等方面,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回家的感觉真好。车子刚离开城区,便驶进了金色的隧道,路边的杨树叶黄了,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金色的光泽,乡村的田野开放着朵朵向日葵,山冈上果园飘香,秋天总是让人盈满丰厚的感激之情。
一家人吃得胃饱肚圆,直到太阳快要融进山巅的树林里,煤火也有些支持不住了的时候,我们才动身把东西搬回家里。
/>那些沉默和忧伤【一】 腊月,我们开始返乡。北风满怀豪情,抵制所有的浮躁和虚幻。眼前要做的是切切实实的事情,排除工作总结的捏造,年终量化的虚假等等。在远方,是一段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长度,那里是我们的老家。我要回去的路并不长,走出本地,跨过一个乡镇即可。棉田早已收整,青青的麦苗泛着鲜绿,早些年并不曾出现此样的情景。棉花价钱大跌,据说我们这里棉花质量不高,纤维度不能达标。村庄的劳力大多外出打工。近年形势好转,有部分人返乡种田。一路有高大的白杨树,方形的田地,新修的水泥路,似乎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宣扬它的富气。 一直以来,回家显得落寂。气宇轩昂,激情万分,满面春光,许多的场景并不能因为物质因素就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西服、领带,骑着车,尽可能地带上一些东西,衣服,香烟,正宗的粮食酒,还有特意思请人书写的春联。很难说清这些实物究竟要去体现些什么,却是要好好准备。进入村庄,村庄之外,我们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界限。矗立的高楼,往来的车辆,高声的吆喝。我们曾经用过的词语,像宁静,静谧,或者清新等等,不再单纯地属于乡村、田野和我们的生活。试着移情于景,一棵树,两棵,三棵。拐弯,再拐弯。 终于有充足的理由回家。在春节。而此前,五一,端午,国庆,中秋,元旦。并不是每一次都有适当的条件。工作加班,赶人情喝酒,外出学习。错过了无法弥补。有时很笨拙地表达着歉意,母亲总是说,谁要你回家了?没有时间就别回来,家里的事情你不要担心,好好搞好你的工作。我无语,因为母亲一个人在家。只是有时提醒母亲,家里的活能做的就做,不一定非得做得比别人强。母亲就是这种性格,在农活上喜欢逞强,三亩田的收入比别人八亩田的收入还要多。我臆断母亲的逞强出自内心的压力。一个人的生活,孤单的每一天,夜晚,无边的黑暗,母亲抗拒着所有的恐惧和思念。我猜测,那笑容,不过是对儿子的关爱,对内心的掩藏,把信心留给我们,独自被痛苦噬咬。 树木黄叶落尽,曾经葱绿的篱笆墙破败不堪。鸡鸭欢快。一段士路,暗淡的灰黄。房屋很夺眼,雪白雪白,和邻居形成鲜明的对衬。我结婚前夕,母亲请来泥匠,用石灰把墙壁重新粉刷一遍。并且像做卫生墙一般,四周及屋檐下全泥上水泥。除去墙壁,还有一套桌椅,新买回的床及床上物品。虽然我在家居住的时间很少,有些物品可以将就着用,但母亲坚持全部换新的。我知道母亲的节俭,但这次,母亲丝毫没有节约一分钱。放倒遮掩的大树,斫去茂盛的灌木,再铲平日积月累的粪堆,禾场填平了,让它升高。整齐,开阔,亮堂。【二】 弟弟来信了。大号油皮信封,厚厚的,沉沉的。母亲迫不急待地递给我。信很短,只有一页纸的内容。我没有读出声,母亲追问信的内容。弟弟从来不会仔细描述自己的生活过程,显得沉默少语。我告诉母亲,弟弟信中只是极为简单且显得敬重的问候,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要担心之类的宽慰话语。我把弟弟寄回来的一叠相片递给母亲看,母亲微笑着,说这张不是在天安门吧?我说是的,就是北京天安门。印象较深的有两张。一张的背景是白天,在天安门广场,穿着休闲服,他和一个朋友相互搭着肩,弟弟显得很严肃,母亲说看他这样子,怎么就不笑一笑呢。另一张是在夜晚,灯火阑珊,弟弟独自倚在一座桥的栏杆上,透着成熟和自信。信中说他现在就在北京市内一家餐馆里打工,主要的工作是配菜,现在已经学习的差不多了,不多久就能自己当师傅。母亲唠叨,餐馆里好是好,就是累,睡得晚却要起得早。 十七岁,弟弟远去打工。母亲一再阻拦,弟弟在家里呆了两年后,执意跟着我的同学走了。我的同学在北京混了四五年,回来的时候,西装革履,半调北京话,在全村甩烟,俨然一幅小老板的派头。他极力劝说,并且保证弟弟的工作。我们满怀信心。谁知同学并没有能给弟弟找一份好工作。弟弟说,到北京的最初是在建筑队里做事,搞了半年,老板仍是不给工钱,同学知道了,带了一帮黑道上的人要去找老板,结果老板逃跑,半年工钱也泡汤。电话中得知此情,知道弟弟一定吃了不少苦,做工程的有哪一项是轻活呢?我提醒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吧。 弟弟的第二个工作是帮人养花喂鸟。我以为这是一项不错的工作,至少不是苦和累的体力活。弟弟说老板对他不错,一起的三个打工仔,他感觉自己是最得老板赏识的。诚实、勤恳、坚韧。这是弟弟身上优秀的品质。这样的场所不会有繁重的体力活,我劝勉他,工程队那么累的活都做了,对于养花喂鸟这类活,一定要细致,要腿脚勤快,嘴巴灵活。弟弟说他买了不少书,曾国藩的《心镜》(后来回家赠送给我)、《小老板的公关与领导艺术》、《卡耐基成功之道》、《中国十大元帅风云》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他说这些书都是从地摊上买的,便宜且有用。我鼓励他,多看书,多学习,总不会是什么坏事情。一年半后,弟弟被老板炒鱿鱼,老板说弟弟喂鱼太马虎,把他的几条金鱼喂死了,于是毫不犹豫地辞了他。弟弟在电话中骂道,他放屁!妈的,这些老板真是精打细算,他说好每隔半年加一次工资,结果说生意不好只加了一次。比我先来的两个工人都被他因为找理由先后辞掉了,倒不是因为我做的好,原来是他在算计我们。老工人要加工资,而新工人来了后要从最低工资开始,他这样做就可以永远给工人开最低价。招工书上说的每半年长一次工资其实是骗人的鬼话。 弟弟从花店出来,找我那同学借了一千元钱,加上几年积攒的,自己租了间房,买了辆三轮车,做起了鲜花的买卖。弟弟先从大的花店进货,再用三轮车把花拖到四处卖。同学说,你弟弟不错,有胆识,有头脑。后来同学又告诉我,其实弟弟做的并不简单。一是这鲜花并不是像白菜萝卜一样,人们每天必买,因此销量不容乐观。另外城管特别严,到处抓人。弟弟每天都要绕道走,钻街走巷,像和城管人员捉迷藏,得处处长后眼睛。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但是弟弟还是经常被城管工作人员抓住。做了大半年的时间,三轮车被没收了三辆,赚的钱全部赔在没收的三轮车上了。 我一直以为,这样的工作方式,三番五次地更换,一味地让老板炒掉,总会让人不能接受。对于我,可能滋生出恐惧、心酸、胆怯。弟弟说,如果这样想,那是极端的错误。很多时候,哪怕老板不炒你,你也要学着把老板炒掉。在外打工,和家里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目的是挣钱,只有不断地更换工作,才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树挪死,但人会挪活。母亲总是在我耳边嘱咐,你弟弟来过电话吗?天凉叫他多穿衣服,让他专心的找一门工作,不要换来换去的,外面坏人多,叫他注意安全,不要和坏人交往等等。我便说,他在外面这么多年,不是一个人生活着好好的嘛。母亲知道弟弟的小心谨慎,但总放心不下。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只好劝慰。村里人传说着我那同学的轶事。说我的同学在外面并不是做什么正当的事,而是加入了黑社会。况且我同学带出去的另外一个本村男孩,几年后回来,就因为抢劫被叛刑。村中有好心的人问母亲,你儿子不是是他带出去的吗?可要注意呀。母亲更回担心,一段时间里寝食不安。 后来,弟弟又做过烤羊肉串,进了几家餐馆。但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有一段时间,弟弟在北京物色了一个地址,准备自己做老板,开个餐馆,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了他的想法,但却因为城市清理,计划成为泡影。时间挥手而逝,弟弟辗转北京、山东、广东、湖北等地,不停地换着工作。最近,弟弟打电话说,总不能在外面打工一辈子,如果可能,想回家开个餐馆。在家里,生活才会显得平静,舒坦,轻松。【三】 按我们的乡俗,大年三十晚,后辈人要买了鞭炮、火纸和香烛到祖先葬地上坟。然后是夜里零点燃放鞭炮,第二天清晨早早起来再放一次鞭炮。其意大概是辞旧迎新,趋邪避鬼之类。多年以来,这几项任务都是我所完成。少了儿时的好奇和兴奋,徒增空洞和虚无。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先是母亲、我、弟弟。尔后弟弟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和我。再后来是母亲,加上我和妻子。三五个人,四方形的饭桌,一人一占据方。母亲总是烧満桌的菜,荤素俱全,有色有香。哪怕剩下多半的菜,毫不可惜。母亲试图用可口的饭菜和红色的布置来营造融洽的气氛,在春节,在喜庆的日子,我们必须学会选择,遗忘过去,才能拥有微笑和快乐。 陈年往事的忧伤,在那年腊月二十八。事件是清晰的,但过程模糊。一切风平浪静后,才明白只有母亲还在身边。幼小的梨树,青青的白菜,未完成学业的儿子。母亲的担子,瞬间圧进千斤重铁。父亲的去世,恍若一场暴雨,让所有的亲朋好友措手不及,疯狂过后,继而是妥协,冷静。丧事如此简单,惟有天翻地覆般的大雪,一切多了肃静与萧瑟,深沉而凝重。突然之间,我长大了。大伯说先去村里找会计贷款,我跟着一同去,解说,保证,签字,附加承诺和责任。时间的推算,坟址的选择,骨灰盒的样式,长辈商量之时,无一不来征求我的看法。十七岁,我必须努力识知身边的事情,学会决断,把握方向。 三亩田梨树,是父亲的心血。换地,买树苗,修剪,守护。三年的时间的呵护,梨树苗茁壮成长。长辈们商量说,梨树不比棉田,需要强壮劳力,最主的是白天黑夜都要守候,要不然一切心血都为小偷而作。我不同意,梨树即将挂果,三年的时间,第一年是一定有好收成的。长辈仍然坚持挖掉梨树,我默然。二亩地的白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母亲和弟弟一起,架了板车,送到镇上的中学。中学校长是同村人,母亲说,去校长说说情,他是会照顾的。我曾经是那位校长的得意门生,母亲找到校长,他很诚恳地接待母亲,结果母亲和弟弟每个星期送一车菜到镇中学,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母亲接过家庭重担,包揽家庭中只有男人才做的一切体力活。耕田、拖土、打药、施肥。一个人做着两个人的事情。母亲本来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现在,更多了一份坚强和倔强。母亲的笑容仍然挂在脸上,自信的笑容,带着风霜和伤痕,像一支悠远的曲子,低诉,怅然,凄美。 我出门上学,母亲让弟弟送我。只有一个背包,我推辞,弟弟坚持。他推出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他骑车,一段路程后,气喘吁吁。中考通知书早已发到手中,弟弟的分数虽说没有达到重点线,却也不错。弟弟的成绩一向不错,初考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进重点初中。但因为家庭,他牺牲了自己的理想,浪费了更多的学习时间。临行前几天,母亲对我们兄弟说,家中二千块钱,哥哥要带一千块的学费和生活费,剩下的一千元,你可以去读高中。不管如何,哥哥的学业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不能中途而废。弟弟没有说话。在路上,我问弟弟,错过读书,就不会再有机会。他坚决地说,是我自己不想读了。一会儿,他又说,哥,有我在家里,你放心。弟弟口中,第一次说出这样化的语言,我愕然,只觉心酸,不知如何回答。【四】 在母亲的期盼中,弟弟终于回来了。弟弟只有春节前后二十天的假期。大叔找人捎信说,现在给弟弟说的那家媳妇,家境不错,一个独生女,长相娇好。母亲说,大叔人很好,很早就张罗着给弟弟操心,大叔说,现在社会,接媳妇或上门做女婿,都是好事,干脆让弟弟到女方家做插门女婿,免得母亲费神操心。母亲解释,这事情还得孩子自己作主,他在外打工,我是作不得主,只有等他自己回来再说。前几桩好事,都因为弟弟没有回家而成为泡影。大叔甚至有些责怪,说这次如果再不过去,也就懒得再操心。母亲让我和弟弟一起到大叔家,大叔见到我们很高兴,立即出门去喊女方的父母。不一会儿,女方父母过来。礼貌的招呼,问候,加上闲谈,查户口般。弟弟寡言,双眼望着别处,一副漫不经心样子。大姨准备了酒菜,要我们同吃午餐。那双亲婉言推诿,我知道这桩戏肯定唱完了。过后,大叔说,那家人嫌弟弟少言木讷,还有就是眼睛,还戴着一副眼镜。大叔说,其实那女孩是见过弟弟的,在大叔家中,女孩对弟弟的人才很满意。近一米七五的个头,有棱有角,我相信弟弟的外表。大叔说那女孩因为和父母的意见不和,一气之下,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大叔还想提了烟酒去解释,弟弟阻拦。事情作罢,母亲知道其中原因,言词中有些埋怨弟弟,不会说话,不会表现。母亲和大叔用心良苦,但本性难移,何况弟弟的本质是好的,诚实,正直,勤劳。 弟弟定好返回日期,母亲说,你要坐的那一趟车的路线,前不久出过事。在一个坡度很大下坡处,突然刹车失效,司机提醒乘客,稳定,坐好,千万不能惊慌。结果还是有一个青年男子自作主张,跳车逃生,却落在另一辆车的车轮下,当场死亡。母亲千叮万嘱,乘车,过河,夜里出门,喝酒,工资,意外等等,啰啰嗦嗦,恨不能把所有担心和期望全部装进弟弟的背包。弟弟在外摸打滚爬许多年,生活的痕迹早已嵌入他稚嫩的肌肤,我理解母亲的顾虑,但更相信弟弟的适应能力。离开家庭,弟弟身上多的是结实和强壮,性格沉默也稳重。 母亲反复地强调,遇到熟悉的人,就要打招呼,这是最基本常识。母亲喜欢拿村里人举例子,什么事情要敢说敢做,只要是对的,不去无中生有。不知道母亲是否针对弟弟在那桩亲事上的态度。十多年时间,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家庭,繁重琐碎的家务,外面的一切往来,母亲都能够独挡一面。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的叹息,在夜里,寂静中,那声音穿透相隔的几堵墙,如锋利的针尖,刺痛我的内心。所有的白昼,显得苍白和虚假。笑容,喧哗,笑话,举手投足的影响,感染我们的是力量,来自家庭生活底部,积极地,有朝气地去对待每一天。母亲所拥有的真实,却在黑夜,是看不到的忧伤和寂寞。 (2005.
大海不会没有汹涌的波涛,人生不会永远顺遂。我们有时会是一只迷失的鸟儿,有着一双强健有力的翅膀,内心却很迷茫,望着白茫茫的广阔的天空,虽不知出口在哪里,却没有丝毫放弃的想法,无论多难多累,都坚持扇动着翅膀,到处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