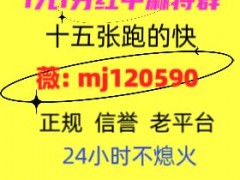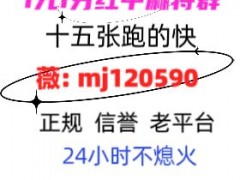微【hh67989或yb54222或xz917430或Q号514737968】欢迎广大麻将爱好者来玩,亲友圈内所有用户都是微信实名制玩家,微信官方授权,安卓、苹果严格审核的游平台游戏!2人3人跑得快红中麻将亲友圈一元一分亲友圈等多种玩法加不上微信就加QQ514737968如果添加频繁就换一个加诚信可免押进亲友圈验亲友圈,满意再补!走过曲曲折折的时光小径,太多的艰辛,曾举目无望,曾无限怀想,曾沐浴花香,也曾与清风共舞。那岁月的馨香,随着潺潺溪流,浸润心田,随着丝丝清风,清爽宜人,即使饱经风霜,心态亦年轻。
我们天台一队的堰塘,修在天顶寨下,紧紧地挨着那条通往寨背后朝阳大队的小公路,从那条公路走下来的至少有四个大队的人,从那条公路走上去的至少有五个大队的人。一个大队千把人呢。这还没算上那些走亲戚的,卖凉粉的,劁猪的,爆苞谷花的,卖锅的,磨菜刀的,做嫁床的。要知道,公社办公地址就在我们天台一队的地方,他们从我们队上征用了不少地,我们天台一队等于就是公社大院的外围基地了。那么你想想,这一条坑坑洼洼的土石公路,得有多少人经过,我们天台一队的鱼,得羡煞多少双眼睛啊。
从海洋涌来的暖湿气流滞留在岷山,带来了无尽的降水。天意。想象中,雨水从天空倒下来,浇在雪山草地,浇在森林里,浇在田地里,通过径流,集聚在溪流沟壑,最终汇入了涪江。涪江在雨幕里变得洪大而暧昧。脱去云的衣裳,剥去雾霭的纱,便看见涪江怪异地奔放和。野性。阴冷。潮湿。神秘。平日空阔的河床满了,气势犹如咆哮的雄狮猛虎。洪水携带着上游的木头、家畜野兽、磨坊房屋、活人死人、瓜果腊肉、军衣军帽,席卷了我们沙地里尚未成熟的玉米花生和椿芽麻柳。巨浪将被呛死呛昏的鱼成堆地送进稻田,送进玉米地。遍体鳞伤。不时有娃娃鱼在泥浪里翻卷,在稻田边呀气。开始还有人捡了鱼回去吃,到后来连娃娃鱼也没人动。没有油,再好的鱼肉也难以下咽。 大洪水过后,河床焕然一新。但焕然一新里有难言的酸楚。学大寨改造的几天前还生长着花生的沙地变成了乱石窖。河坎齐刷刷倒塌,一大边秧田玉米地消失了,几人合抱的桐子树不翼而飞。漩水掀翻了挑水路薄弱的沙坎,把一两户人家悬在了河岸上。木头在乱石滩堆积如山,但没有人敢动。广播里在反复强调,谁敢发混难财谁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再说,大地震就要来了,谁还稀罕那些吃不得的木头? 大洪水过后是一次次的中小洪水。浮柴浮物没有先前多了,但沉柴却多了起来,而这样的沉柴是允许私人打捞的。白天,属于生产队的劳动力不得打捞沉柴,如果打捞,也是要被判作破坏“抗震救灾”的,至少被判作“搞资本主义”。夜晚有人捞沉柴。马灯,或者手电。雨一霎一霎,火把是不管用的。我不属于生产队的劳动力,我有捞柴的权利和自由。沉柴想象不到的多。不仅有陈柴,更有新柴。连根树充斥了缓水区域。死水里一摞摞的柴棒,让我们探索的脚兴奋不已。浅滩上,大小不等的树木时隐时现,勾引着我们的眼睛。队长见一个孩子居然能捞到堆山塞海的柴,便动员劳动力都来捞,为集体的砖瓦厂捞。别的生产队见了,也都来捞。这下,龙嘴子人山人海,尤其是出柴最多的水域,差不多人镶人。用我们自己的话说,“跟插玉米包包一样”。有站在岸上的,有涉水的,挤成一团,柴网挨柴网,柴网挂柴网。沉柴被捞上岸,堆成山。一个生产队一山。 捞柴是龙嘴子独特的风景。人山遮住了半边河,柴山遮住了半边河滩。男人捞,女人背。也有女人、小孩捞的。所谓捞,就是踩在水中,将绑有绳网的长杆扎入深水里,等柴满了,再收起来。麻绳织的网,钢筋做的圈,枫树做的杆。有捞到野物的,有捞到家畜腊肉的,甚至有捞到死人的。捞到死人,往河里一推,死人便又跟洪水走了。我们都吃过打捞到的野物和腊肉。雨一个劲地下,捞柴的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也有裹塑料布穿雨衣的,也有无遮无拦任雨水泡的。背柴的脸上一股水淌,屁股上一股水流。1976就是这样。白天为公,夜里为私。马灯在龙嘴子的夜里晃荡。河水再次暴涨,不知不觉中要淹了河滩。只听得乱脚踏水,一片大呼小叫。为了保命,人们不得不放弃柴山,放弃背篼、马灯和柴网。有涉水过深或起心太大为抓住一根大柴被洪水卷走的。每每那时,人们只有目送的份。有骑在木头上漂流一两里路才沉没的。救命的喊叫被浊浪撕得粉碎,弥漫着蚯蚓的腥味。
/> 在废墟之上 ……想到死亡是来结束他的晚年,替他解脱辛劳的。他朝火焰走去。火焰没有吞噬他的皮肉,而是不烫不灼地抚慰他,淹没了他。他宽慰地、惭愧地、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 ——博尔赫斯《环形废墟》 我对自己说了太多的话,以至于,在这个春天的晚上,听着水声冒着气泡,不停地在我身后翻滚,我已经像一个枯朽的树干,无动于衷。温度持续走低,我在想着明天早上要穿上寒服出门。以物资的温暖抵御内心的寒冷。我无法知道能不能将自己挽救,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我只能知道,死亡还远,我的废墟在这个春天无比地灿烂,甚至是嫣红得耀眼。并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巨大的幻觉中,我无法逃离。 这是因为,我一次次地想起梦境,在这个将我包围的梦境之中,我恍然成为一个少年,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少年。在一片像沼泽的废墟之上,我看到了那个在我生命中出没了多年的女人。在河塘,白莲、红莲、绿水织成的一张网中,我又回到了有鬼神出没的月光下。这是一个更早的年代,我的知觉从那个乡村里来到现在,已经是岁月足够的沧桑了。这岁月变成了我的一张脸。在我幻想的爱人中,成为一种红颜薄命的影子。在这个背景里,我的母亲已从一个年轻、憔悴的少妇变成了老太婆,但我却一次次的愧疚着她对我无边无际的爱。而我的父亲,我们只不过是血缘上的父子,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吃菜,他更多希望我是一个不依赖任何人的男人,我对于接受父亲的爱,感到过无形的压力。在这样的多年的关系中,我看到了我的女人。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热爱她,当她像一条藤蔓将我缠绕,将我窒息在一颗不死不活的树上时,我多少次感到我的时日不多,但是当她离去,当我在黑夜中,我又是多么的惊恐。人类在创造男人的一半时,就在幻觉中给了这世界一把刀,将身体凌迟,一块块地分割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也许这不是梦境,也许这不是我从河塘魔幻般的月光下逃出来,所寻找的另一种魔幻之镜。在以后的多年中,每一次看到水面,我都觉得莲花在黑夜里朝我开放,淡淡的花香使我迷醉,渐渐地找不到返回的路途。我多么热爱的我的幻觉。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为我诞生的另一个女人。她有许多瞬间,挥舞长袖,在黑夜里引领我奔跑。在船头,在一条永远流动的河上,在一条上了岸的小路上,当闪电从空中霹雳,她的美貌如河塘的莲花向我绽放。当闪电过后,铺天盖地的雨水,让我的身边在大片的黑暗中颤抖,而漆黑的树林和粘湿的地面上,我就成了一个摇晃的木偶。我再怎么呼喊,我的母亲都已不在面前,我的父亲好像不在人世。当我转身,巨大的树冠,在我的头顶拼命地摇晃,我已经无法控制肉体的颠簸,肉体像一个被大水击垮的破木船。我的河塘,已失去了它的引诱神秘和美好的能力。它看起来更像我的宿命中无法逃脱的沼泽。 从早年出走,到现在蜗居在一个黑暗中的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巢穴,我已经掏空身下的地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废墟,在幻觉中出现的,方型的、圆形的、还是星光性的、弯月型的,我无法知道它们具体的形状,它们不停地变化交叉,我穿行在这个巨大的迷宫中。 当我知道,太阳从东西升起,从东边落下,一个少女的影子从我身边过去,我突然地大哭不止。事实上并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停留下来。事实上我要的东西,在目光里转瞬积即逝。 我开始寻找我的女人。这个女人,代替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在一条狭长的有着零星花香的小路上,且歌且舞。在我的血液里,激起绚烂的水花,犹如早年的河塘,在大水泛滥时,它们一次次地泛起光芒。雪白的,激烈的,我惊心动魄的花朵。我在追逐嬉戏中,完成了少年的岁月。 我咀嚼着风中飘荡着各种植物的气息,满怀枯涩地来到今天。我的故人相继去世的消息带着莲花朵上的光环,在我品尝自己去日无多的人生时,成为了一种美丽。而我,在这样的时刻小心地出让自己的孤独。因为热爱而悲伤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想着我的女人在另外的前方,或者我们正在不同的小路,朝着太阳落下的田野走着。在这个真实的幻觉中,拥抱着她到来和离去的知觉。 在我的大地之上,我重新知道死亡必定来到任何人的晚年,有个人像我的兄弟,在我身体里成为我的影子,我们一起搀扶着,成为一道火焰,在我多次回忆中出现的河塘上,成为一次次炽热的燃烧,它们把我的灵魂变成一块块发光金属碎片,到处洒落。在我所经过的地方,不但有照耀黑暗的光芒,还能一次次的让我怀念女人离去之前的天空。那里有云朵,有我鲜血染红的流水,有至死不会改变的月色。我将她从幻影中救出,安慰着自己,我一层层地翻上异地岁月的山岗,不畏辛劳,宽慰地等着死亡送上一朵微笑的花朵。 那么,即使我知道,亲人们从我的身边走掉,并死亡……我不安着,等待什么降临,但是我仍心存疑问:我的女人从远方来,还是从身边走开?一生当中,我拥有了自己的所有吗?或者,我担心过我是她的幻影?我拥抱着这个温暖的幻觉,向自己内心寻找着答案。在有莲花开过河塘的过去和现在,乃至于死亡的那一端。我行动在自己的废墟之上,是不是正完成着一个人开始或者一个结束,灵魂在生命当中,真正地成为了无比容光的一件大事? 想着这些,我已经看到了我落花遍地的废墟,正慢慢地凸起那朵梦中的莲花,我的眼泪在这个注定的时刻,已经成为一道红色的光芒。2006年3月12日
而人生,不期而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