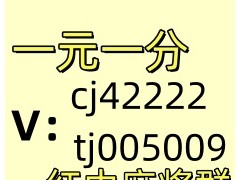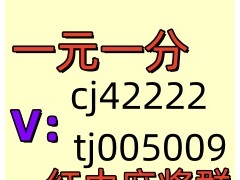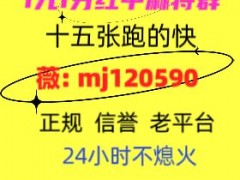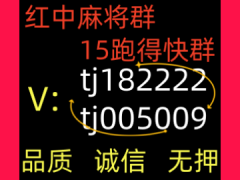不知是气候差异还是什么原因,同回的矿工妈妈,生下的宝宝无一存活
我落地后也是气息微弱,不会哭泣
接生婆把我放到了烂席卷上,准备扔掉,被折腾的九死一生的妈妈,还在昏迷中
爸不舍得扔掉我,抱着一线希望,嘴对嘴地吸出了我胸腔里的残留羊水
我哭出了声音,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妈妈没奶喂我,那时奶粉稀缺,买不到,经济又困难,妈妈只好用葡萄糖和着稀面水代替奶粉喂我
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长得黄瘦赢弱,多灾多病
常听妈说,一晚上要起床喂我好多次,把好多次尿,习惯性地要用嘴对着我的额头试几次体温……
那些小到不许再小的详细,往日不过一点小絮叨,此刻却成了相互不复接洽的破口
恐怕有一天某一句话,让大师都怒发冲冠,结果城市不胜的摆脱
以是为了制止如许的截止,很多人在功夫的激动下会渐渐地冷淡少许人,彼此不复有接洽,是一种自愿也是一种场合
人生这场路程,是个举世无双的历尽沧桑
虽说不是那么顺利,可若能一部分径自宁静地走完,又岂能说、不是完备的究竟!即享用了凄美的宁静,又不会烦恼谁的寰球,只释怀静意地实行那份属于本人的工作;大概,如许的路程,才是极了的!
就如许,我定下了两张铁鸟票,大略的整理行装,便带她回到了朔方
我该去纽西兰吗?塔斯曼寒冬的海水当面,白种人的寰球再有一片土
澳洲已清闲天边,纽西兰,更在天边除外除外
庞但是阔的新陆地,澳门大学利亚,此后地从来蔓延,连连接绵,蔓延到帕斯和达尔文,南岸,对着塔斯曼的冰海,北岸,浸在暖脚的南宁靖洋里
澳洲人本人抱怨,说,不管去什么国度都太远太遥,常常,向朔方飞,骑“奔放士”的风波奔驰了四个钟点,还没有跨出澳洲的大门